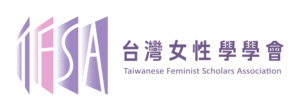一場必要之秀
2005/06/17 – [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A15版]
《觀念平台》一場必要之秀
【張君玫】
西蒙波娃說,有些女人把自己變成花束,有些化成博物館,有些則是難解的象形文字。當女人被摒除在超越性的國度之外,把自身當成物品來妝點,便成為她最溫暖的存在主義實踐,藉此追求一種永恆。
在文化差異並列以及商品邏輯的結合之下,自我博物館化的欲望方興未艾,很難斷定好壞。並列的表象掩蓋了文化政治的權力不均等,但至少是一種「發聲」的方式。就算進不了博物館,你也得把自己當成一則時尚宣告,或是透過照相、錄影和自傳書寫變成一則值得開啟的檔案,彷彿唯有如此,才能在碎片激流的後現代社會中得到些許確切的存在感。
喜歡博物館的不只是西蒙波娃的女人,或LV的秋冬發表會,還有全世界各國的政客和文化政策制定者。全世界倖存的原住民幾乎都被博物館化了,唯有透過遊客的觀看,原住民的文化生存權才得以被見證,並暫且忘卻他們在政經社會文化上的苦悶與磨難。
至於那些沒有被博物館化的原住民呢?很抱歉,他們早已在歷史中滅絕。人類歷史上的「地理發現」是用鮮血寫的。就拿海地這個比台灣小一點的島嶼來說,現在的海地人絕大部分是十六世紀末被法國殖民者從非洲「輸入」的奴隸後裔,而最先為海地島命名的阿拉瓦克斯人呢?早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不久就被西班牙人滅絕了。每一次的「發現」,都在人類歷史再一次啟動了馬克斯所言的「血淋淋的原始積累」。
回顧日本殖民政權挾帶國家機器的武力對台灣原住民所進行的掠奪和屠殺,再聽聽日前台聯聲明中所稱「高金素梅和她的族人在靖國神社外的抗議是『非禮』日本」,我們知道,至少在對原住民的態度上,日據時代的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早已形成了意識形態的共謀。高金素梅確實「非禮」了日本──如果以「禮」相待意味著演出一個溫馴可愛的被殖民者的話。或許,台灣的殖民論述與後殖民論述中找不到「原住民」的位置,因為他們和西蒙波娃所看到的「女人」一樣,早已被摒除在超越性的啟蒙理想之外,更因為「原住民」的苦難所見證的正是啟蒙計畫本身的破產。
從博物館化的欲望,到脫離靖國神社的訴求,這本身已經是一個解除殖民枷鎖的象徵。沒有錯,高金素梅和她的族人是如此素樸的運動者,沒有擲地有聲的論述。當日本強勢警力阻擋,族人坐困遊覽車上,高金素梅只有受挫的眼淚和「日本人怎麼可以這樣欺負人」的痛訴。媒體呈現給我們的發言則是「親中」對抗「親日」的言論布局,而不是任何關於原住民歷史命運與抵抗權的探討。「親中」、「親日」之類的國家主義說詞與統獨化約論,向來扮演著台灣政治語言的eas y code,輕易把所有的檔案加密,免除一切深入的歷史反省與改寫。
有人說,高金素梅在「作秀」。我說,有何不可?由台灣的原住民來演出一個「不溫馴的被殖民者」,這正是一場必要之秀──提醒我們,在國家主義的思想暴力之外,在逛博物館的視覺高度之外,不妨多一點感性去想像那些真實的苦難與流血死去的人們,多一點理性去追憶她╱他們存在過又被抹去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