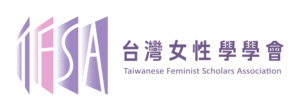生命的定義與戰爭
生命的定義與戰爭
王秀雲
生命的定義是什麼?有生物學課本定義為「生長、運動、形態、遺傳、感應、代謝」,也有從生命的物質基礎來定義生命,因而有所謂:「生命的物質基礎是蛋白質和核酸;生命運動的本質特徵是不斷自我更新,是一個不斷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的開放系統。」這些定義雖然看起來很明確,卻是既抽象又充滿了令人生畏的專業名詞,而生命的定義還是難以具象化。
事實上,這個問題自古以來不知困擾了世界各地多少的思想家及學者,哲學家、歷史學家、宗教家、生物學家等都不可避免地會碰觸到這個問題。而在這方面的討論與著作,也不知用了多少噸的墨水、砍了多少棵樹,或占用了多少電腦記憶體。是幸也是不幸,這個問題似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解決。然而這個仍然可以辯論的問題,確有許多人因為種種因素而採取了特定的立場,並且據以針對許多事物加以道德的判斷。
最近在台灣有關墮胎思考期的爭議,反應了生命的定義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與複雜性。爭議的雙方分別是婦女團體和以「尊重生命大聯盟」為主的宗教人士。前者主張婦女應有身體自主權,可以選擇是否墮胎,後者則主張墮胎是攸關胎兒生命的大事,因而主張在施行人工流產前需要一個強制思考期。筆者無意在本文中判斷是非曲直,而是想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那就是生命的定義究竟是從何而來?有了生命的定義之後有什麼樣的後果?目前台灣一般所談的生命的定義,是古今中外皆然的知識嗎?
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今天所承襲的生命的開始的說法,是來自近代科學的一些發展。其中影響最深遠的可能是生命的重新定義、生命意義的窄化,以及在這個新定義下的生命崇拜。
根據20世紀的科學觀點,生命的開始在精子與卵子結合的那一瞬間。因為這個版本取得了典範性的位置,加上胚胎顯像的具體化,使得關於生命抽象的想像或是辯論相形失色,人們把這些可見的影像直接定義為生命。這個定義當然不局限於科學家的實驗室或科學教科書,宗教界(特別是天主教)很快地沿用,而任何有礙或有害生命存在的行為都成為可議,甚至被攻擊。
在過去,生命的起點是在嬰兒落地時或是當孕婦可以感受到胎動時,然而現在嬰兒出生已經不是真正的起點了,而是當胚胎還是一團渾沌的組織時。這個起點與過去我們對生命的了解所不同的是,在過去我們理解的生命是具體的一個嬰兒,然而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渾沌的影像,如果沒有科學家的指點與說明,我們基本上是不會認出來那就是一個生命,因為渾沌組織畢竟還是很不成形的。
這個胚胎雖然「不成人形」,我們卻不能小看它在現代人類社會中的地位。它不但擁有了身為生命的崇高地位,也因此有所謂的人權。台灣的宗教團體甚至把人工流產與罪犯的死刑相提並論,從胚胎人權的角度來談人工流產,儼然主張一個受精卵與一個人有相等的地位。多年來在美國的反墮胎人士一直強調墮胎不論早晚都是謀殺生命,顯然是根據受精就是生命的開始的定義。
或許是因為這個生命定義的力量難以抵擋,支持墮胎合法化的往往避開生命的問題而把重點放在婦女本身的選擇問題。正反兩方多年的爭執結果之一,就是強制規定欲進行人工流產的婦女必須觀看一段胚胎發育(也就是所謂生命的開始)的影片,企圖使婦女回心轉意。在台灣,似乎許多婦女也認為(甚至想像)懷孕是有一個人的「生命」在肚子裡,迫不得已必須墮胎時往往要受道德與肉體兩方面的煎熬。
20世紀中期之後,由於生物科技的發展,特別是超音波技術的發展,孕婦的肚皮變成透明可見。只要超音波一照,肚子裡是什麼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也可以判斷胎兒是不是正常。生命現在搖身一變成為相當具體的影像,不管是胚胎、胎兒或嬰兒的影像都變成是生命的展現,充斥在婦女及一般大眾科普雜誌裡,積極地提供大眾生命的意義與實體。
婦產科診所最令許多剛懷孕的婦女興奮與滿足的產品之一,莫過於那一張超音波儀器裡印出的胚胎影像,即使這個生命(胚胎)看起來既不像真人也不像嬰兒,但孕婦們都人手一張,並驚奇於科技的威力。
總之,我們雖然還是繼續用「一塊肉」與「投胎」的說法,但是這些表達方式的意義已經有了轉變。人們開始說「肚子裡的小生命」(生命有輕重大小可言嗎?),孕婦死亡則稱「一屍兩命」。此外,不同物種生命的發展過程也可見於科普刊物,例如我們可見人類胚胎與其他動物胚胎在不同時期的並列對照,以及最後顯示的人類獨特性與重要性。
比較之下,過去不管任何人都無法看透孕婦的肚子,這種不可見度因此造成一種神祕的不確定性。在過去,生命的定義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辯論不休的話題,生命的定義可說相當多元化,而生命到底從何時開始更是不明確。懷孕的產物常被指為「肚子裡的一塊肉」,這塊肉在出娘胎之前是相當模糊而難界定的,因此貍貓換太子的故事是如此地生動,而關於人生出非人的動物常也見於民間傳說。
另外,根據民間信仰,所謂的胎是沒有靈魂的,不然怎會有「趕著去投胎」的說法,當然也不能稱它為生命(現代台灣的嬰靈祭拜基本上是來自20世紀日本的習俗,加上商品化的結果)。
在過去,無論暴露身體的哪一部分都是不雅與不妥的,這個原則基本上也包括孕婦的肚子,不要說看孕婦的肚子裡面,就連(公開)看孕婦肚皮都是很不適宜的。即使在20世紀中期,胚胎的圖片影像仍僅出現在教科書裡,而不是像現在四處可見(包括尊重生命大聯盟的網站)。假若過去的人可以乘時光機到現代來看到胚胎的照片,不知會有多驚駭?也許他們會認為現代人很野蠻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當展現生命的胚胎逐漸成為神聖不可冒犯時,對胚胎的崇拜與對墮胎婦女的譴責基本上是一體兩面。胚胎不再只是孕婦肚子裡的一塊肉,它的超音波影像出現在許多的場合中,並藉由高曝光率的電視廣告、教科書、婦產科的資訊傳單等成為一種公共的議題。
當屬於私人的事物被轉化成公共議題之後,女性的身體權就成了問題。生命的擁護者總以為墮胎的婦女是冒犯了生命的神聖性,然而婦女在做有關控制生育的決定時所面對的問題,包括經濟、道德、壓力、愛情關係,以及社會缺乏良好育兒的環境等實際的問題,卻彷彿都變成次要的問題了。
對於過去大多數的婦女而言,所謂「人生」是多孕多產多無奈,甚至是危險重重。晚清大臣曾國藩的女兒曾紀芬的一生中有高達13次的生產紀錄,從頭到尾跨越了二十幾年,也就是說她的一生中有大半的時間是處於懷孕的狀態。雖然曾紀芬曾企圖利用藥方來流產,但並未成功。曾紀芬與許多貧民階級婦女的差別在於,她雖然不想如此多產,但還是可以負擔得起扶養13個子女,而後者往往要訴諸殺嬰來控制家中人口(當然,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下,受害者往往是女嬰)。
在曾紀芬回憶她企圖流產未成的例子裡,似乎沒有背負著現代婦女因墮胎所帶來的道德壓力,她的動機完全是基於現實的考量(健康問題)。在她回憶這段過往時,我們沒有看到她內心的掙扎,也沒有聽到她關於生命的意義或開始的內在辯論,倒是感受到她因失敗而帶來的無奈。
相較之下,現代婦女在處理她們的生殖問題時所要面對的,不但有來自西方科學的生命始於授精的那一瞬間的新定義,還有來自日本的嬰靈信仰,更不用提社會的壓力與感情方面的煎熬了。到底是曾紀芬時代的女性還是我們現代的女性比較幸運?關鍵可能不在科技進步本身所帶來的便利,而是這些進步所牽涉到的許多複雜的改變,這包括我們的世界觀裡的生命的意義。
王秀雲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