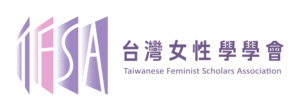請不要祝我母親節快樂
請不要祝我母親節快樂
蕭蘋、游美惠、唐文慧、楊巧玲、李佳燕、林芬慧
前記:我們是一群具有母親身份的社會學、教育、傳播、醫學、和資訊管理等領域的研究者,因為感受到做母親的苦,我們組織了一個討論母職的讀書會(我們的網站「母職狂想曲」即將在http: //sctnet.edu.tw上完成建立),想要以我們的專長來探索、和解開母親身份的奧秘。我們思考、和研究的成果除了將以學術的方式發表外,我們更希望在大眾媒體上公開表達,與所有關心這個議題的人分享。這是我們共同完成的第一篇著作。
在母親節,請不要祝母親快樂。
因為這個社會在每年僅有的一天中所提供給母親的快樂方式,是選擇有限的消費(只有化妝品、衣飾、瘦身、和家電等與母職相配的用品促銷),和召喚母親檢驗自己是否及格的道德標準的放大(比如:每年必有的模範母親的選拔)。
如果能瞭解大多數的母親在大多數的時間,因為這個身份,而不快樂,然後進一步探索何以致之的原因(先別像平常一樣歸罪「母親很神經質」這樣的個人原因),也許才可以讓天下的母親得到被理解、和被支持的快樂。
什麼是母親呢?什麼是母職?對於不同時代的母親,我們都會在心中描繪出不同的圖像。有關我們上一代的母親圖像,呈現出來的大多是家庭主婦,教育和知識水平低於父親,在30歲以前就已完成她的生育責任,生完3-5個小孩(其中至少要有一個男孩),剩下來的人生就是努力讓先生無後顧之憂、將孩子拉拔長大。在家裡 (幾乎是她活動的全部區域),她有做不完的家事,說不完的嘮叨,和操不完的煩心。
我們這一代的母親呢?現象上開始有一些不同。我們比較晚婚,也比較「老」才做媽媽。我們的教育水平已提升至和另一半相去不遠、甚至並駕齊驅的程度,因此我們可以在外謀得一份工作,這個工作不只是對個人(尊嚴)、或對家庭(小家庭需要兩份薪水的維持)的經濟上的需要而已,心理上,我們也害怕重蹈上一代母親的覆轍,過著沒有尊嚴、否定自我的不快樂生活。
然而,事情沒有這麼容易。事實上,我們這一代的母親仍然沒有得到多少的尊嚴。在工作上,母親的角色很少被真正的同情,有了孩子通常被老板、和同僚假設是對工作的一大阻礙,或在玩笑中暗示這是妳縱慾的結果。更教人心驚的是,在家裡(除了工作之外,這仍然是我們活動的一個主要區域),仍然有做不完的家事,說不完的嘮叨,和操不完的煩心。是的,與上一代不同,我們擁有了一些自我,不過這自我拉扯、分裂、破碎在事業成就、和家庭孩子之間。我們,做為母親,仍然沒有快樂。
整體而言,這一代的母親較上一代向前進了兩步(社會、經濟地位的改變),但同時也倒退一步—背負了更多的負擔。到這裡,誰還有勇氣再進一步設想(望著我們的女兒的臉),下一代的母親呢?她們的未來是什麼?
為什麼母親不快樂?為什麼母親都很緊張?為什麼母親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她在和誰做比較?許多相關的研究發現,人類的文化普遍在建構一種有關母親、母性、和母職的神話。這一套神話定義了女人的重要角色,和規範和這個角色所有相關的價值和行為。在這個神話的籠罩之下,一個女人一生的終極實現就是要成為母親,否則將會有遺憾,甚至成為她的人生的一個無法彌補的缺陷。這個神話還告訴母親,除了生養小孩之外,還得要打理所有的家務,而這些工作彼此之間並不會互相衝突,因為只要心中有「愛」,就可以排除萬難。因此,當媽媽的人,必定都喜歡當媽媽,喜歡作餵奶、換尿布、洗衣、煮飯等「媽媽的工作」。而且,這種「無盡又深厚」的母愛對孩子永遠是好的,永不嫌多!
這一套神話影響廣大,大部分的女人,不管已婚或未婚,不管已經當媽媽或未曾當過媽媽,多多少少都受到這一套神話建構的左右。所以已婚的女人「當然」要生兒育女當媽媽,不婚、和未婚的女人也希望能達成自己的「一生的終極實現」-要生個小孩證明些什麼!(好像一個女人沒有成為母親,就是個心理、或生理「不正常的」女人嗎?)而未婚的男人總是期待自己未來的老婆就是未來孩子的媽(難道不能只當太太不當媽?)。而女人當了媽媽之後,就要在時間的分配上,完全以家庭、子女為主要優先,若想努力追求自我成長與生涯發展,就會有揮之不去的「罪惡感」縈繞在心。即使只是企求有自己一點的「私生活」-暫時拋下孩子去從事自己的社交生活或娛樂活動,也難免自問「我是個好媽媽嗎?我會不會太自私?」等問題,彷彿善待自己就會背離當「好媽媽」的光環。
反觀父職角色,則很少充塞這種自責與罪惡感。有太多的「新好男人」只要洗洗碗、倒倒垃圾、或是陪小孩玩耍、寫作業,就覺得自己比鄰居的爸爸、或比其他已經當爸爸的人都好太多了。沒有相對應的父親神話建構的威脅,願意從事父職實踐的父親,總是顯得比較從容、大而化之、和有自信;對父職毫不在意者,更是理直氣壯地不必懷有絲毫的罪惡感。
台灣作家簡媜的作品「紅嬰仔」,是呈現母親經驗與形象的一本暢銷書。這本書訴說她個人的育嬰史,其陳述的過程即一再的建立、和鞏固母親的神話。整本書除了少部分提及女性的母職經驗的「窒息感」與「疲累」之外,大多在抒發為人母「再辛苦也值得」的滿足和喜悅。母親神話在她的生花妙筆的包裝之下更添美感,但也更教人心驚膽跳,因為性別關係再次被徹底的去政治化了。舉例來說,當寫到一個大學時的女友的墮胎經驗時,簡媜將這個經驗和東方文化中神秘的嬰靈傳說連結一起:
有一年到日本旅行,無意發現供奉嬰靈的小廟,每個小泥偶代表一名仍被父母記憶的小孩…
我添了香油錢,祝福每個小小孩。後來,還寄一張照片給她,特別說明也祝福了她的小小孩。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不知道遠嫁約翰威尼斯堡、擁有熱熱鬧鬧幸福的她如何回想那年的故事?…她是否還記得十九歲時,她哀哀慾絕卻仍以一個「母親」的堅定口吻說:
「不管以後…我活還是死…有沒有生小孩…他永遠是我的第一個孩子!」
算數的,只要曾在子宮裡住下來,即使只有一個月,女人也會以母親的愛收容他、記憶他、思念它、緊緊擁抱他。
一個短暫的、未曾開始多久即結束的母親經驗,顯然的要跟隨這個女人一輩子,即使她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得到了「熱熱鬧鬧的幸福」,也不能忘懷(總有人會提醒的,作者做為朋友即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在這裡,母親的神話得到絲毫不加思索的加強:一個女人一旦成為母親,即終身為「母親」,即使她的孩子還未出世即消失、或先她而死。之後,母親的角色也成為定義這個女人的最主要方式。
是的,所有的女性也都不知不覺的在承受、和參與這樣的神話建構,否則如何能「自然」、又「歡喜甘願」的承擔做母親的重責大任。在這樣的過程裏,隱忍痛苦、犧牲自我的是「好母親」(最極致的表現是每年母親節選出的「模範母親」),可以受到社會的褒揚;追求自我快樂、和成就的則是「壞母親」。好、壞之間,是一條楚河漢界的鴻溝,中間沒有連結的橋樑。
簡媜在「紅嬰仔」的書裏,不是沒有反省到「我們的社會本質上是歧異婦女與兒童的」,但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後,她用更多的篇幅說明,好母親可以盡個人的力量來調整、和克盡母職,壞母親則吝於調整個人,以至於可能造成自己、和孩子的毀滅:
一個盡責的母親沒辦法等待社會變文明才哺育幼嬰。即使崩石擊中她的頭顱,昏厥之前,若懷中嬰兒索奶,她也會用最後一絲力氣解開衣衫把乳頭送入嬰兒嘴裏。社會對她搖頭,她只好靠自己的力量做好母親工作。
然而,我也必須承認,不願承擔母親責任的人亦多有所聞。她們優先想到自的利益與感受,是極度吝嗇的媽媽,或者,她們一直無法處理好自己的人生,以至於身心承受巨大壓力,甚至造成精神疾病。
她們之中,有人把自己的小孩活活打死。
這個單一、僵固的好、壞母親的分野,是我們的文化裏,一個嚴重的病。得過美國國家書獎的作家Betty J. Lifton以她做為養女的經驗,研究被收養者的心路歷程。她引用心理學的理論指出,我們都會把自己的母親劃分成好壞兩種人格,那麼每個人其實都有兩個母親。Lifton說,「根據理論,我們的心理學功課,就是到最後能夠瞭解,兩個母親其實是同一個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但我們的文化,似乎從來沒有長大過,堅固的壓抑母親做為一個真實、完整的個人需求,最後「母親」只成為一個扁平、僵化的象徵。
在這裏我們並非否定母親、和孩子之間所存在的真實親密關係,相反的我們珍視這樣親密的關係的普遍性與價值;我們也不否認從事孩子教養的重要性,相反的我們認為孩子的教養十分重要,重要到需要更多人、甚至社會機構的參與,才能完成。不過重點是這種親子之間親密關係的維持、與孩子教養的進行,不能、也不應單靠母親、以及母親的自我犧牲來進行,它可以有多種形式的展現,讓每一個真實的母親依自己的生活條件、和所處的社會脈絡(包括:階級、種族等),做合適的選擇、和安排,而不必有任何的罪惡感。在這個關係裏,是開放的,每個相關的人(尤其是父親)、和社會機構都應該參與進來,分擔相同的責任。
首先,母親、母性、和母職,必須從文化做重新的定義,還給女人自由,這些自由包括:身體的自由、自我實現的自由、和自我選擇的自由。我們肯定,一個自由的、突破壓抑限制、並能享受自我成就滿足的母親,才能為孩子的未來帶來新的想像。
CNN的記者、曾被選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拉丁美洲人的Maria Hinojosa提到,她在童年時,她的母親讓她不必上學,而去參加一場示威活動。對Hinojosa而言,「從此,爭取正義成為我生命的中心」。美國巴納德學院院長Judith Shapiro自述母親和自己的關係,
成功的女人常常要不是有一個把她們當成兒子看待的父親,就是有一個突破壓抑的母親。這些壓抑限制了女人的成就,以及女人對其成就所能享有的滿足的程度。我自己就是屬於第二種。我不但有幸得到父母雙方持續的支持、愛和鼓勵,尤其重要的是,我有一個了解我的志向的母親,她從來不會根據社會對我們兩代女人所定義的生活方式,給我或她自己設下限制…她總是鼓勵我們「躍向太陽」。
在台灣,有沒有可能找到這樣的另類母親的典範、或容許這樣的母親形象出現的空間?
當然我們不會簡單的說,做一個自由的母親,在現在的情況下會比較快樂,因為這也同樣落入個人選擇的迷思中,別人會在你受挫(主要來自親人、或社會無形的責難)時,輕鬆的說「這是你個人的選擇」。
我們主張,母親或母職定義的改變,除了在文化上的改變外,還必須有政策、和社會制度上的改變來配合。如果我們逐一檢視和母職有關的政策,就可以瞭解我們的社會是如何漠視、甚至懲罰母親。
首先一個女人從懷孕開始,有沒有良好的醫療照顧體系支持她的身體健康,而不是對身體過度醫療化的介入?
她能否愉快的繼續做身體和心理能勝任工作,而不因為懷孕被雇主歧視或解雇?
她有沒有機會獲得與懷孕有關的所有訊息和知識,而非被錯誤的教導懷孕生產是女人的天職和本能所以不必學習?
在產後,孩子成為母親最大的壓力來源,這個社會有沒有提供母親有薪資給付的育嬰假?
有沒有在社區提供令母親安心、方便又廉價的托兒設施?
有沒有讓父親有參與育兒的社會制度設計(如:父親的陪產假、育嬰假和家庭照顧假)?
有沒有讓社區居民共同來關懷母親的辛勞和孩子的成長?
如果要回答以上這些問題,那麼幾乎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或只有少部份的肯定。這些國家、和社會應該進行的對母親照顧工作,卻被理所當然的忽視,而要母親個人自行調整、和承擔,然後在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時,只提供一些「口舌服務」給母親,推崇她們很「偉大」,這是何其的虛偽與殘酷?
在母親節,我們身為母親,認真的檢視這個看似「自然天賦」、實則充塞「社會建構」痕跡的身份,我們有真實的參與孩子的生命成長所得到的快樂,但也感受到更多需要衝撞突破、強加給女性的枷鎖。在這一天請你傾聽母親真實的聲音,給我們支持,讓我們自由。
(本文經過中國時報編輯略加刪改,曾發表在2001年5月13日母親節中國時報人間副刊)